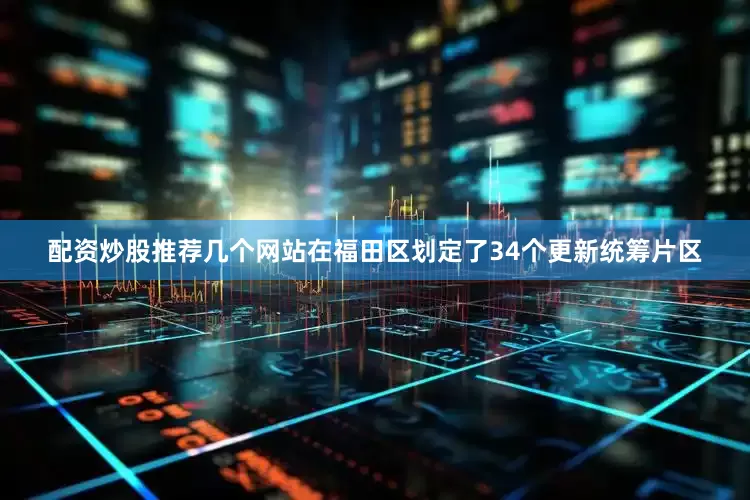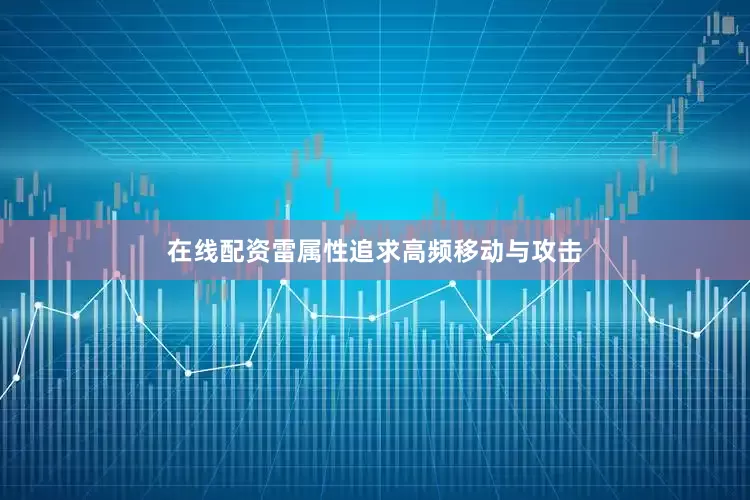1947年3月,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34个旅25万人马,从南、西、北三个方向大举进攻陕北解放区,企图一举攻占延安,摧毁中共中央。当时,共产党在陕北的正规军加地方部队只有4万余人,众寡悬殊。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从整个中国革命的大局出发,不计较一城一池之得失,撤离延安,率领中央机关部分人员开始了艰苦转战。从1947年3月18日离开延安到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毛泽东转战陕北历时1年零5天,行程1000多公里,途经12个县(延安、延川、清涧、子长、绥德、子洲、靖边、安塞、横山、米脂、葭县、吴堡——以第一次经过时间为序),驻留过38个村庄(榆林33个、延安5个),时间最短的仅几个小时,最长的达4个月,超过1个月的村庄有王家湾、小河、神泉堡、杨家沟。
为保护中共中央安全转战,彻底摧毁蒋介石的“擒王”策略,陕甘宁边区的各级党政机关、军警民组织以保护革命领袖为第一要务,多次在紧要关头保卫了中共中央,在安保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安保工作整体部署为外围保卫和内层保卫两大方面。
外围保卫
外围保卫工作在前线和敌后广泛开展,主要分为三方面:一是西北野战军通过军事行动调动敌军主力,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增大党中央在陕北的回旋余地;二是边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侦察敌情,袭扰敌军,干扰敌方对党中央的位置判断;三是在敌方内部潜伏人员进行情报截取和干扰,及时提供敌军行动计划,使中共中央在转战路上游刃有余。
展开剩余91%主力保卫
1947年初,为了迎击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北野战兵团,所有驻陕甘宁边区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统归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和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挥。这支只有2万余人的部队,在粮食、弹药供应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肩负起保卫中共中央安全转战陕北的重任。
3月初,野战军以一部兵力出击陇东,以调动准备进攻延安的国民党军。同时,彭德怀调新4旅16团守卫延安机场,边区教导旅警备7团5000多人严阵以待,延属军分区民兵和游击队埋设地雷,破坏道路。经过七天顽强阻击,迟滞、消耗了敌人,为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和边区机关、群众安全撤离延安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派兵北进,欲寻找西北野战军主力决战。西北野战军诱敌深入,于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歼敌1.4万余人,沉重打击了胡宗南集团,初步稳定了西北战局。6月8日,毛泽东转移到靖边王家湾时,距敌仅隔一道山梁,四五百米,危险至极。彭德怀立即派王震率一个旅,并命令三边和绥德地方部队及游击队全部火速支援,猛攻敌军侧背,吸引敌军退出天赐湾,成功为中共中央解围。8月18日,中共中央沿葭芦河转移时,刘戡部穷追不舍,彭德怀急令许光达率领第3纵队火速赶往乌龙铺、曹庄一带,截击敌人,顺利接应和掩护中央机关安全转移。
小河会议后,中共中央制定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中原突破”的军事策略。自8月始,西北野战军在数月内两次攻打榆林,虽未攻克榆林城,但进一步削弱了北线敌军的力量,调动了胡宗南部10个旅北上增援。8月20日,西北野战军适时转移兵力,准备在沙家店开战。毛泽东在战前曾说过:“沙家店打得好,我们就转危为安,不走了;打不好,我们再向西走,进沙漠。”最终,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一举歼灭敌整编第36师主力6000余人,直接扭转了西北战场局势,自卫战争转入内线反攻。随后,西北野战军在延清战役中取得胜利,收复了延长、延川、清涧、子长、绥德等城及延安东北广大地区。
到10月中旬,西北野战军兵力已发展壮大至7.5万人,其中不乏起义、收编的国民党部队。为了稳固加强军事力量,西北野战军在1947年冬至1948年春进行了以“诉苦”和“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大大提高了部队政治觉悟和技战术水平。毛泽东对这一创造性的整军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
西北野战军通过数次作战,成功巩固了陕甘宁边区,使南线胡宗南部不敢轻易冒进,北线榆林22军只有守城之力,威胁渐无,最重要的是为中共中央增加了很大的回旋余地。
游击保卫
胡宗南部大举进犯陕北后,陕甘宁边区政权机构迅速进入战时状态,积极配合军队开展游击战争。边区政府保安处(简称“边保”)随地委机关撤出城市,在乡村指导游击战争。在各地普遍成立的游击队伍中,各级公安部门负责人大多担任游击队长,各级党委书记担任政委,游击队以保安处的干部和保安队、警卫队为骨干,吸收民兵和群众参加。游击队伍充分发扬解放军一贯擅长的游击战术精髓,利用精干敏捷的优势,处处袭扰敌人,打击敌人小股武装,截获敌掉队人员及辎重部队,组织群众盘查放哨,侦察敌军动向,警戒捕捉特务、叛徒,动员群众支援前线,配合主力部队运动作战。
1947年3月,边保下辖的保卫团一分为二,其中四个连先在延安城附近担任警戒,后到安塞监视胡宗南军动向,并先后参加配合西北野战军在陕北的数次战役。4月7日,边保总处机关改编为第7大队,下设三个中队,其中1中队专门负责前线敌情侦察。边保副处长赵苍璧率领一支由100多名侦察、情报人员组成的前方侦察工作队,带着一部电台,深入延安东、西、南三条战线,采取“迎着敌军侦察,夹着敌军走”的策略,及时掌握敌军宿营、行军动向,动员群众坚壁清野,组织开展游击战斗。在侦察活动中,通过抓俘虏、派出小分队、化装混入敌占区、了解情况,将获得的情报及时用电台报告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1947年5月底,敌5万大军向中共中央驻地王家湾包抄而来。形势危急,赵苍璧急派侦察工作队潜伏至蟠龙镇以北秘密侦察,架设电台做好准备。在监视敌军动向的第五天早晨,工作队员成功监视到敌军踪迹,立即报告后方。工作队尽管只有几条枪,但还是果断阻击,拖延敌行军速度。最终,由于及时得到情报,中央机关顺利北撤,脱离危险。
1947年6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处长周兴发表文章《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代表中共西北局发出号召。敌军入侵之后的短短三个月,边区游击队已经发展到7663人,长短枪4592支,轻机枪15挺,共作战114次,毙伤敌614名,俘虏1281名。不久后,赵苍璧率30多名工作队员和马万里带领的一个警卫营共400余人,在咸榆公路绥德、葭县地段侦察、骚扰敌人。8月中旬,中共中央转移到绥德,敌军分几路进抵欲歼灭之。赵苍璧带领队伍成功吸引到了敌北进的一路快速部队的注意,却也遭到了包围,处境十分危险。赵苍璧沉着应变,避敌锋芒,带队突出重围,成功牵制了敌军这支先锋部队,将其带离了中共中央的行动路线,使毛泽东等得以顺着安全路线向葭县转移。
情报保卫
抗战胜利后,国共关系剑拔弩张,中共中央坚持“兵马未动,谍报先行”的思想,大力加强情报工作,向敌后布置众多情报力量,以便及时掌握敌军动态。转战陕北期间,中央后委、中央社会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等机构在情报信息方面取得了大量成绩,确保中共中央在陕北征途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前,决定联合中央城市工作部和中央社会部等情报机构成立一个联合秘书处,由周恩来领导,一手抓军事作战,一手抓情报作战。周恩来还负责接收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罗青长上报的绝密情报。
在中共众多的情报力量中,最出名的便是被誉为“龙潭后三杰”之首的熊向晖。早在1937年,熊向晖就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到胡宗南身边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后来当上其贴身秘书,开始接触国民党的核心机密,并在两次紧要关头成功地保卫了中共中央。第一次是在1943年夏,胡宗南得到密令闪击延安,熊向晖将计划上报延安,中共通过舆论攻势,迫使蒋介石放弃进攻。第二次是在1947年3月,熊向晖提前看到国民党“闪击延安”的方案,冒着极大风险通过西安地下情报系统将敌军进攻陕北的兵力部署、行动路线以及空军配合等细节及时报送延安。当胡宗南的高级将领尚不知情的时候,其进攻计划就已经到了毛泽东的案头,中共中央得以从容撤离延安。由于熊向晖在情报战方面作出的突出成绩,毛泽东称赞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
自卫战争初期,为了全力支持军队作战侦察的需要,边保将自己领导的前方侦察小队和情报电台全数交给西北野战军,还在敌内部广泛安插内线、发展人员为我所用。毛培春是边保南线情报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人物。1938年,他从边保七里铺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第一期毕业后,顺利打入阎锡山部从事地下工作,后加入军统,担任西安宪兵司令部特高组中校参谋。在1947年8月沙家店战役时,毛培春传送了敌军调动、配置的重要情报,为西北野战军打赢歼灭战提供了信息保障。1948年4月,毛培春奉边保指示,随敌军撤退时,混乱中遭敌机扫射,壮烈牺牲。
自卫战争期间,中央后委统管后勤工作,负责通信保障和情报搜集。中共中央在陕北转战途中,为了避开敌方电台侦察,不敢架设大功率电台,有时还要保持电台静默。中央后委撤到山西后,在后方广架电报转播台,通过总结各战场的作战情况和作战经验,为中共中央正确决策提供了前提条件。由于通信得到保障,我方甚至可以对敌进行情报干扰。有一次,周恩来命令放出假情报,蒋介石错误判断中共总部在绥德,命令胡宗南向绥德进攻。实际上,毛泽东隐藏在400多公里外的王家湾,从容地在陕北小山沟里指挥着全国解放战争。
在转战陕北的一年里,尽管胡宗南始终在费尽心机地寻找中共中央,企图消灭之或驱赶其东渡黄河,但毛泽东总能对敌军行动了如指掌,指挥中央机关坚持留在陕北,或在敌军追堵的夹缝中穿梭往来,或在敌军到达前安全转移,还时不时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最终挫败了胡宗南的图谋。
地方政府安全保卫点滴
地方政府在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安全保卫工作。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将部分保卫工作编录如下:
最后撤出延安
1947年3月,党中央获悉情报,敌人已调集几十架飞机包括一个伞兵中队到西安,准备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为严防敌军伞兵空降延安,周恩来带领李克农、赵苍璧及中央警卫团、边区保卫团的负责人,一起翻山越岭,对延安周围的防空阵地进行了视察,布置了警戒,配置了高射武器,在军民中进行了防空和打伞兵教育。同时,赵苍璧还奉命率边区保卫团破坏东关飞机场至延安城的公路,以防敌人突然袭击。
3月18日晚,原定向北撤退的党中央,临时改变路线,向东经飞机场撤离。由于中央行动保密,边区保卫团的战士不知道毛泽东要经过机场,所以在执行破坏机场的任务时,也将机场旁边的公路挖了几条壕沟。时值陕北冰消季节,被破坏的机场公路泥泞不堪,难以通行。一旦党中央不能顺利通过,滞留在路上,将成为敌机轰炸的目标,情况十分危急。赵苍璧闻讯后立即飞骑赶到机场,组织人员连夜修路填沟,保证了中央机关在夜色掩护下撤离延安。待党中央顺利通过后,再次将填好的路破坏。19日凌晨,边区保卫团在扑灭了杨家岭礼堂的大火后,集中于清凉山上监视敌人,直到敌人占领宝塔山、凤凰山并抵达延安城边,才从容撤退,是最后一支撤离延安的部队。
榆林地区公安保卫纪实
1947年3月,宁夏马鸿逵部由西向东进犯三边地区,并在4月3日攻占定边。国民党军虽占据县城,但只是困守城中,与广大农村地区和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解放战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战事发生以来,定边、安边等县都在原警卫队、保安干部的基础上成立了游击队,保护县委县政府转移,将在押犯人移交后方,并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武装斗争。定边县游击队由武装科长白天章兼任大队长,县委书记郝玉山兼任政治委员。安边县游击队由原三边社会部干事李福盛任指导员。
定边失守后不久,西北野战军总部给三边地委、军分区下达了一道绝密命令。据李福盛回忆,命令大意是“党中央、毛主席没有离开边区,正在陕北指挥着西北战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现在党中央已经转移到靖边县境内。总部首长要求三边分区的所有地方武装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堵住来自西线和北线的敌人,绝不允许其中任何一股危害党中央的安全。同时要严守机密,绝不允许泄露中央的行踪”。
毛泽东还留在陕北的消息,给三边军民打了一针强心剂,三边分区党政军在党中央和西北野战军总部的直接领导下,立即展开行动,全力以赴地投入保卫党中央的工作中。
1947年11月22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来到了米脂县杨家沟,在此处停留长达四个月之久。杨家沟有陕北最大的窑洞庄园——马氏庄园,庄园内72户地主聚族而居,设山寨自卫。毛泽东和周恩来居住的新院,是留日学生马醒民采用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亲自设计、监修的私宅,不仅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而且窑洞内部构造精妙,暗道取暖,三通纳凉。毛泽东来之前就派人作过调查,结论是杨家沟的群众基础和生活条件都很好。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这里的地主大多是支持共产党的开明士绅,出过中共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延安市市长马豫章等许多共产党人。毛泽东来了后,马家地主不仅积极让出窑洞提供住宿,还拿出粮食解决部队吃饭问题。
毛泽东在杨家沟期间,米脂成为全国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为了保证毛泽东安全,杨家沟附近布置了周密的保卫措施,沟里有中央警卫部队,沟外有边保的保安团和游击队,10公里外的吕家沟是西北野战军总部,多层防卫,内紧外松。同时,杨家沟的地主、居民不外迁,不会走漏风声,而且沟口一卡,外面的特务也进不来。看似普通的小山沟,却让毛泽东安全居住了四个月,备好的防空洞一次都没有用上。有一次,毛泽东提出要到米脂的双泉堡李继迁寨(今属横山县)看看,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带领警卫战士走在前头,途中遇到一座独木桥,桥下河水湍急。毛泽东正要过桥时,周兴担心木桥不牢,便带人先作试探,结果几个战士一到桥上,桥就坍塌了。周兴赶忙带领干部、战士连夜抢修渡桥,保证毛泽东安全渡河,到达目的地。
东渡黄河
1948年春,为有利于指挥全国战争,党中央决定东渡黄河,与工委、后委会合。3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开会决定,让汪东兴负责东渡黄河事宜,争取在十天之内完成东渡的所有准备工作。毛泽东给汪东兴派了一个连的兵力,以便在准备工作中充当劳力,在渡河时承担警卫工作任务。此外,还派了1部电台、1名话务员、1名译电员,以方便汪东兴随时向党中央报告准备工作情况。汪东兴深知这次东渡黄河事关重大,必须紧紧依靠当地政府和群众,因此又带上政治部搞宣传和群众工作的干部各2人,协助渡河准备工作。
汪东兴带人马进驻吴堡县川口村,选择这里为东渡地点。为了不走漏风声,对外统一宣称是“旅长”要过河。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封锁了附近的黄河滩头和渡口,并修筑了许多防空工事,布置了防空炮火,同时严格盘查来往行人,限制地主、富农等人的活动范围。
3月12日,汪东兴找来吴堡县委书记、县公安局长和陕甘宁边区保卫处、社会处处长等人开会,安排人员购买麻绳、撑杆、木料,筹备100多人十天用的粮食和几十匹牲口所需的草料。来到渡口后,汪东兴发现渡河还面临着一些问题:一是渡船不够,只有3只,其中2只还存在漏水或船帮损坏问题;二是船工不足,只有3人,临时补充船工的话,担心渡河技术不够熟练;三是时值黄河化冰,河面有上游冲下的流冰,对船只造成威胁。
时间紧、任务重,汪东兴立即找来人修补破损船只,并派人调集渡船。当时,川口已成立了水手工会,工会奉命调集了8只比较结实的木船,准备用5只渡人,3只渡骡马和行李,所有船底都铺了木板,木板上面又铺了席子。此外又调集了许多船工,所选船工大多是技术过硬、政治可靠的党员和贫农。针对黄河流凌问题,大家集思广益,采取了几项防范措施:一是每只船上,安排2名冰情观察员,每人备一根撑竿,随时准备推开冰块,保证船只的安全;二是用麻绳把木料捆绑在一起,每只船上备几捆,万一船被冰块撞翻,就用木捆救生;三是每只船上至少安排3名会游泳的人员,以防不测。一切准备就绪后,从16日开始,所有渡船每天在黄河上演练两次,为正式渡河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3月21日,毛泽东离开杨家沟,经过两天行军,于23日11时左右到达吴堡县川口渡口。毛泽东见到汪东兴后,听取了关于渡河准备工作的汇报,非常满意,在与前来送行的县委、县政府同志和乡亲们一一握手告别之后,踏上了渡船。下午1时左右,开始东渡。按照事先安排,毛泽东和家人上了第一只木船,周恩来、任弼时等人上了第二只木船,陆定一、胡乔木等人上了第三只木船。据时任川口水手工会指导员、东渡时给毛泽东掌舵的薛海玉回忆,毛泽东乘坐的木船最大最结实,本来一只渡船上有9个船工(1人掌舵,8人扳船)就足够了,但为了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他特意挑选出14名船工(2人掌舵,12人扳船)负责这只船。
渡船安全渡过黄河后,顺利到达对岸碛口镇高家塔村河滩上。毛泽东离开了陕北,向新的驻地走去。3月23日晚上,汪东兴护送毛泽东东渡完毕后,又返回川口村,开会叮嘱地方群众和同志,首长过河一定要保密。随后,经过几天的摆渡,中央机关及警卫部队剩余的700多人全部渡过黄河,跟随毛泽东继续奔赴其他解放区工作。
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在渡河前,对前来送行的人们说:“请转达我对陕北老乡的问候,谢谢他们一年多来对我们大力支持。告诉陕北人民,我们不会忘记他们对共产党、对人民解放军的一片深情和友谊。”毛泽东渡过黄河后,更是站在岸边伫立西望,半晌后,深情地说:“陕北是个好地方!”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东渡黄河后,结束了陕北转战的征途。党中央通过一年零五天的运筹帷幄,历经1000多公里的风雨兼程,不仅把敌人牵制在陕北,盘活全国,实现了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并且制定了大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纲领,明确了夺取全国胜利的路线方针政策。
(田建发 冯 帆)
发布于:北京市辽宁股票配资公司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